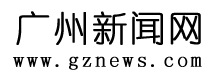吴聚平
童年与故乡,是写作者跨不过去的两大母题。莫言先生把文学的故乡称为一个人的“血地”。我的散文集《似是故人来》,也离不开对生我养我那个故乡的回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乡。我所处和书写的乡村,是过去三十年的乡土,它们正处于历史大变革中,时代的变迁反映到人与事物的身上,我敏感于这些变化,唏嘘于那些命运,做了本能的记录。
打有记忆起,我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白天缠磨在她身边,晚上与她睡在一起。我的祖母像许多农村老人一样,七十多岁了还在田头灶尾间爬摸,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沟壑,却不妨碍她灵魂的活跃。这活跃让她常常处于无休止地讲述当中。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坐在床头,抽着旱烟斗,讲述开始变得深沉而绵长起来。
这个时候, 小小的我就成了她的听众。她的讲述既有流传已久的客家“古仔”,如“田螺精”“老虎外婆”“蛇精”等,也有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她用一口客家话,绘声绘色地讲着,让坐在床头另一边的我睡意全无。如今,那些故事细节我已记不太清,但我永远忘不了一个老人在回忆往事时在草烟缭绕笼罩下的那一份激动,它们穿越时光,成为我脑海里永恒的画面。
如果说祖母在我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那么成长路上一位位良师益友的启发与鼓励,则让种子最终得以萌芽、开花。
少年时代,我有幸遇到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蓝彩容老师。蓝老师充满了教育热情,带着一群乡村孩子读优秀的课外作品,并要求我们学会观察身边的小事,让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写日记成为我与自己对话的重要方式,成为写作的开端。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同时也是我的堂姐吴利平老师,常把我的习作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初三时,吴伟老师对我的小诗和散文进行了详细的点评与指导,在他鼓励下我成了当时学校文学社的社长。作家梦,也悄然成了一个隐秘的梦想。上大学后,我开始尝试短篇小说的创作,给我们上新闻写作课的赵国政教授,在我一篇习作后面,用红色钢笔郑重地写下这样的评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希望你把写作当作一种事业,一种生活方式,坚持下去”。
是的,写作不仅是自我倾诉,更是一种使命与召唤。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杂志社,成为一名采编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写作开始变得密集,内容大多以财经新闻、人物访谈、评论为主。后来我从传统媒体出来,但并没有停止书写,我在新浪博客上写,在豆瓣上写,后来在微信公众号上写。在野生写作的十多年间,我的大学班主任杨励轩老师、师弟杨金运、闺蜜梅子、小阮等是我的忠实读者,他们总是默默地给我留言、转发,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好友兼大姐姐赵玲给了我热忱有益的意见,让我试着走下去。从未谋面的读者雷夫,给予我的文章真诚的反馈。借本书的出版,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祖母和那些有故事的夜晚;感谢我的父母、亲人们对我的爱、包容与帮助;感谢在文学的道路上给予我各种帮助与指导的良师益友们;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时代出版社原总编辑张秀枫老师、华南师范大学黄雪敏教授,为我的小说作评论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周建江教授,为本书写评论的“资深读者”雷夫,为本书出版奔忙的县文联、作协领导及文友们;最后我要感谢读者们,“真喜欢你的文字”“希望能读到作者更多的文章”……我默默收藏着这些评论。
最近两年,我的写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故乡回望,祖母讲过的那些故事在我的心中始终没有远去。写下它们,不是出于理性的深思熟虑,而是情感的自然而至。
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身体深处的那个小女孩回来了,原来她一直没有远去。当我辨认出她时,内心里是有些佩服她的。她拥有的想象与诗意,是此时的我所未能及的。她对生活真谛的体验胜过此时的我不知多少,还有一颗通透而纯真的心。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一座消逝了的村庄,看到许多曾经出现在生命中的人,他们从时光深处走到我的眼前,常常让我眼前一热。那个世界在重新打望时苏醒了。
那个坐在狗尾巴草垛上劈柴的少年,出神地望着日落处的天边和远山。山的那一边,就是远方了吗?多想像一只鸟一样飞起来,飞到天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个爬到山顶俯瞰村庄的少年,看着山脚下盒子一样的房屋,人们就在这些盒子里生,死后再归后面的山。天地合围,便是他们的宇宙。
在山里待久了,寂静的宇宙开始说话了。一朵花,一粒灰尘,好像都在对少年诉说,她听到了山的私语,每一声的风声,都似乎别有含义。她闻到了特别的味道,那是一种野气。日后,她终于明白这样的时光就是孤独。捡一颗山石,高高举起扔到山下去,让它发出沉闷的一声回响。
我一生的幻想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来源:河源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