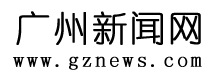李凤梅
我父亲的二哥,我叫二爹。二爹是村小学的教师。
印象中的二爹,留着小平头,身穿卡其布北京蓝中山装。独来独往,不苟言笑。
我从小就有些怕二爹。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里,还是在田间地头,只要我碰到他,便会绕路一溜烟跑开。
用母亲的话说,我就是一条上不得台面的夹尾巴狗。
但就是我这样一条夹尾巴狗,却在二爹面前做了一件让我至今仍觉骄傲的事。
那事发生在我小学四年级期末考试的考场上。我们就读的村小学是回水乡第二中学小学。按惯例,每年期末,周边几个大队的小学都集中到我们学校考试。而且所有考生都是打乱来坐。那次,我们考室的监考老师就是二爹——李老师。
语文考试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间,我愕然发现,前排的男生居然在偷偷摸摸翻书。
翻书?作弊?
这怎么行?
我心中的正义感、无畏感油然而生。“李老师,他翻书!”我的手指直直地指着前排的作弊男。
那作弊男闻言,吓得一哆嗦,先是慌忙合上了书,再是装模作样趴在课桌上写题。
而我则一愣一愣地望着二爹,一颗心怦怦乱跳。我不知道二爹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我甚至有些后悔,怕二爹怪我多管闲事,扰乱考场秩序。
站在窗边的二爹,无法掩饰些许错愕的表情。也许在他多年的监考生涯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当场举报作弊吧。而且,举报人还是一个平时看到他就会掉头逃跑的小不点。
二爹先是望了我一眼,那眼神看似平静,而我却从中读到了鼓励和赞赏。然后,他径直走到那个作弊男面前,一把收走了那本书。二爹不怒而威,让那个作弊男瑟瑟发抖。
痛快!敞亮!
但很快我就发现,那个作弊男不断扭过头来,不断用一双鼠眼愤恨地瞪我。还不时摆出一副要我好看的表情。
贼眉鼠眼!我冷哼一声,朝那家伙翻了个白眼。
虽然“邪不压正”这句话让我面无惧色,但“小鬼难缠”这句话却让我内心动荡不安。
铃声响起,交卷。我背着书包慌慌张张穿过校园。校园里熙熙攘攘,我却感到阵阵寒意。我不断警惕着回头,生怕一不小心就挨上一闷棍,脑子里不断闪现自己被暴打的凄惨情景。我不怕挨打,不怕受痛。我怕正义挨打,怕正义受痛。真的怕。
突然,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冲到了我面前。他们嗷嗷叫唤着问,是不是我举报了人家作弊,人家要打我。
果不其然!我虽心头一惊,却嘴硬道:“不晓得哟。”
男同学们嗷嗷叫唤着喊:“你不要怕,有我们!”
于是,我这只上不得台面的夹尾巴狗,成了众人簇拥的英雄。于是,我这只丑小鸭,有了护花使者。
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发放成绩单那天,班主任谭老师特意在班上表扬了我。
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年后,回想起此事,才明白应该是二爹把我举报作弊的事告诉了同学和老师。
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明白做人一定要一身正气。也正是这一身正气,让我无论身处任何境地,都觉得自带光芒。
我上五年级时,二爹由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也成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当时的感觉是:怕什么来什么!
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山村小学,老师们上课都是照本宣科,平淡如水,根本无法满足我们那颗好奇的心,也根本无法激起我们的求知欲。
二爹的课,让我有了惊喜。
穿着北京蓝中山装的二爹,会带我们观察校门口那棵根如盘龙的黄果树,会和我们讲中国四大名著,会和我们讲学校的来历,会和我们讲“伴月星”。多年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的标题就是——《伴月星》。
那时候,小学一、二年级用铅笔,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用钢笔。而墨水瓶是断断不会拿去学校的。有次,我忘了让钢笔在家喝饱墨水,只好趁着二爹和老师们在操场摆龙门阵的空档,壮着肚子推开二爹的寝室门。
油漆斑驳的桌子上,除了墨水瓶,还有一摞试卷。很显然,就是前两天的单元测试试卷。好奇心驱使我,朝那试卷上瞄去。嗯,有两张试卷已经批改了,孤孤单单躺在一旁。仔细一看,那两张试卷只批改了阅读部分。再仔细一看,那两张试卷,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堂妹的。
嗯,有点奇怪,为什么先批改我和堂妹的试卷?而且都只批改了阅读部分?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从那以后,很多时候我都去二爹的寝室里吸墨水。又有一次,我去吸墨水的时候,发现桌子上的单元试卷,又是先批改了我和堂妹的试卷,而且又是先批改了阅读部分。
很显然,这绝对不是巧合!那这件奇怪的事说明了什么呢?
凭我有限的分析能力,我只能想到三点:一是通过我和堂妹两个人的试卷做对比,以便更好掌握全班同学的学习情况;二是二爹很重视我;三是阅读很重要。
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一直以来处处受人白眼。突然有一天知道有人在默默关注我、重视我,而且这个人还是最会教书的老师,是全村最有文化的人,我真是感到心尖都在颤抖。
后来,我外出工作,很少回老家,也就很少再见到二爹。心中却时刻挂念。
前几年,我拖家带口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也如愿见到了二爹。他呆坐在屋檐下,苍老得让人不敢相信,苍老得让人心疼,眼神暗淡、腰背弯曲、头发花白稀疏。身上的北京蓝中山装,已被黑色的棉袄取代。退休后的二爹,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钻心之痛。我堂哥,那个全村最有出息的仔,突发疾病,英年早逝。我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当我见到二爹的那一刹那,我信了。我的心也随着二爹面部的抽动,一下一下,钻心的痛。
二爹除了发呆,就是独自一人到学校转悠。一旦发现墙垮了、梁塌了、瓦溜了,就会急急忙忙找来师傅帮忙维修。然而,学校早已合并到镇中心小学,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天井里的那一左一右的紫荆花树和桂花树,独自花开,独自花落。
前几日,也就是教师节前夕,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二爹病逝了。二爹在弥留之际交代,要将他葬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
我挂上电话,擦去泪珠,打开电脑。我要让二爹,要让这位最后的乡村教师,活在我的文字里。
来源:韶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