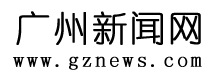茉 白
九月,奶奶小花园里的花陆续凋了。
凤仙花枝头坠着一个个毛茸茸的“豆囊”,渐渐从淡绿褪成淡黄,外皮被秋阳晒得枯干薄脆,一阵风把它吹落在地上,沙砾般的棕色种子便跳脱出来。傲然枝头的鸡冠花到了秋天也耷拉下头,俯首称臣了一夏天的花穗纷纷倒戈,吐出黑芝麻似的种子。我为花落叹息,可当手里捧着密密麻麻的种子时,却油然生出一种踏实的盼望。原来,每一朵枯萎背后,都攒着一段生生不息的轮回。
奶奶说,秋天是攒出来的。枫叶攒着变红的秋霜,小草攒着明年的根须,鱼儿攒着繁殖的鱼肥,松鼠攒着过冬的橡子,农人攒着丰收的粮食。“那我们攒什么呢?”我疑惑地追寻答案。奶奶说,我们攒着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可奶奶平时攒的只是碎布头和我丢掉的糖纸。童年的我没什么玩具,除了晴天和小伙伴采花草,雨天就只能看着窗外发呆。奶奶挑了几块茜草色的碎布头,沿四周边缘处缝上细密如蚂蚁大小的针脚,快收口时抓一小把红豆灌满,在她的穿针引线下,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套玩具——六个棱角分明的小沙包。奶奶还教我玩法,她那古铜色瘦削的手,动作敏捷、上下翻飞,看得我惊羡不已。还有一次,我回到家,发现窗框里别着一个轱辘轱辘转的风车,外皮是绿色光面纸,里子是银色铝箔纸,中心处还绘有一对红虾,那是我吃完虾条的包装袋,那时我最喜欢看《大风车》栏目,却遗憾自己没见过真的风车。奶奶竟偷偷攒着我的小小愿望,帮我一一实现。
后来,奶奶生病需要静养,我被送到姥姥家住了几个月。爸爸接我回奶奶家时恰逢春节刚过,奶奶正坐在窗前剥瓜子,一粒一粒灰中透白的瓜子瓤,与她灰麻的头发有着相似的苍凉和缄默,已积成一座小山了。见了我,奶奶耷拉的眼角又弯成扬起的帆,兜满了春风和笑意,忙把两个烘在暖气上的红橘子塞到我怀里,将堆满瓜子瓤的盘子推向我,又一角一角地展开五六层白手帕,最后一角被掀开时,露出六块月牙似的橘子糖,奶奶手里就像托着一朵渐次绽开花瓣的水仙花,雪白的瓣,淡黄的蕊,一缕缕淡淡的甜香萦怀。我一手捏起两块橘子糖,一手抓一把瓜子瓤,嚼得满口香甜,嚼着嚼着,眼泪忽然打湿了鼻尖。爸爸嗔怪我,正月里的哭什么,我也莫名其妙地委屈,不知自己为何鼻头一酸。现在回想起来,大抵是一颗小小的心被奶奶日夜攒起的想念和疼爱塞得满满的,自然而然地溢了出来。
长大后,我才明白奶奶一辈子不识字也没有工作,她表达爱的方式不像其他长辈那样直截了当地给红包买礼物,而是默默攒着自己的心意,一厘一寸、一点一滴地攒着,攒在剥了一天的瓜子瓤里,攒在层层叠叠的手帕深处,攒在那双无比灵巧却隐现着淡褐色老年斑的手中,攒着攒着,那些情愫就生出了腿脚,不知不觉地跑到我心里去。
常常觉得奶奶就像秋天,带给我童年的温馨和缤纷,即便一天天的枯萎衰败,却把生命最后的养分供给稚嫩的我,为我,千千万万次。那一点点攒出来的记忆足够温润地滋养我走过人生的四季。细细想来,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智慧的沉淀、卓见与胆识……也都是一点点攒出来的,一如秋深,一叶叶、一声声,在我们的人生中渐次抵达浓郁。
来源:湛江晚报